
在我们这山里,扁豆是极寻常的。
父亲的菜园子里一年四季瓜菜飘香,斑斓五彩,红的是苋,绿的是椒,紫的是茄,就算最不济的冬日,园子里也有白菜萝卜帮衬着撑门面,可是父亲的菜园里却没有扁豆的影儿。
扁豆像旧时人家里的偏房或是外室,进不了正经园子,仿佛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菜。
到哪儿去寻呢,倒也不远的,就在家门前的斜坡土坎上。开春,父亲在坎上掏了两个小土坑儿,埋了几颗扁豆籽儿,顺便洒了点儿草木灰,怕四邻淘气的鸡啊猪啊,又在周遭围了一圈刺楞楞的杉木枝儿,好了,随它了。

父亲忙碌得很,得闲就一趟趟地往菜园子里跑,送水啊,添粪啊,薅草啊,松土啊,侍候得比自家孩子还要周全。扁豆在土坎上瞥见了,倒也不急不恼,它仿佛知事乖巧的孩儿,并不怪罪主人家的怠慢。我们呢,正是疯也似玩的年纪,天天从坎上坎下来来回回,却也没有停下来瞄它一眼的意思,扁豆啊,在它的整个萌萌的青春期,真个是舅舅不怜,姥姥不爱!

也不知道是哪一天,扁豆就疯也似的蓬蓬勃勃起来。原本就没有给它搭什么架子,父亲种它的时候,大约就想到了,随它丰俭由人吧,扁豆就自顾自地满地攀爬,它野性,却也神性,仿佛长了眼睛,最后竟然攀到坎上别人家菜园子的篱笆上,织了厚厚一面绿墙,满架紫色的扁豆花引来蜂蝶嘤嘤嗡嗡,我们这才留意到这土坎上突然膨大的一群,枝蔓纵横,出世横空,只是现如今,原本荒寂空旷的土坎一下子显得局促了好多,一株小小的扁豆开动乡野,却也是这般轰轰烈烈风云雷动。

不过几番风滋雨露,小小的镰刀状的扁豆就结了满棚满架,父亲才想到该采摘了,父亲站在土坎的边上,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兴奋,只是显出奋力的样子,面对着这样庞复的一群,攀摘起来倒不是那么容易了,不一会儿,手中的小簸箕里就见了尖。

晚上就会有这样一道菜,新采的扁豆斜切成丝,配上辣椒丝儿,锅烧热了,滚油大火急炒,最后洒上点黑皮豆豉炝锅,这样一盘豉香辣香更兼扁豆微微苦涩里蓄着清香的菜肴,是很能下饭的,但不知道为什么,母亲却很少做,父亲菜园子里的那些菜蔬都排起队儿的想挤进家里的餐桌呢,扁豆啊,哪怕结了满筐满架,却也不被主妇赏识,我为扁豆鸣不平。
扁豆虽然一直备受冷落,但有一样却是其它的菜蔬比不上的,那就是扁豆的一生拥有太多的芳名。

最早的时候,遁着父辈们的方言俚语,我一直以为扁豆的浑名叫蛤蟆豆,且暗地里思忖了好多回,意期发现这镰刀状的豆子与蛤蟆可有神似之处,最终的结局不甚了了,除了肤色皆为青绿之外,扁豆与蛤蟆实在相去甚远。文友清欢知我唤扁豆为蛤蟆豆,深以为好笑,她告诉我,扁豆的学名叫蛾眉豆,取其长长的镰刀样类于女子蛾眉弯弯,我好像突然有茅塞顿开之感,原来我叫了那么久的蛤蟆豆,竟然是我自顾自给取的,相比之下,蛾眉豆就优雅文气多了,简直改变了我脑海中这么多年,对于扁豆感觉粗粝土气不入流气质的臆想,所谓的名不正,则言不顺,岂止是言不顺,简直是无以言了,这是我在扁豆身上得到的最为深切的感受。

文友思文兄也写过扁豆的,只是他比我要渊博厚学得太多,他一气道出了扁豆的众多芳名,学名,浑名,雅名,在他的文字里,我才知道,扁豆又叫沿篱豆,蛾眉豆,膨皮豆,刚皮豆,等等,这些名字都比我的蛤蟆豆要生动许多,细细品咂,这一串的名字也串起了扁豆的生长史,沿了篱笆攀援,结了状如蛾眉的豆子,又因表皮硬韧,显得刚性十足,而且我还知道了,扁豆不仅可以供蔬,还可以入药,能健脾和中,还能消暑化湿。
我总算为扁豆寻得了一些安慰,据我所知,无论南北西东,辣椒从来就叫做辣椒,黄瓜从来就叫做黄瓜,可在我们这小小的荒僻之地,扁豆却一下子拥有这么多的名字,恰恰证明了,貌似偏居一隅倍受冷落的扁豆,其实得到了太多人的关注,只是长久以来,在人们的观念里,它是一份额外的花红,因为不曾为它劳心费力,也并不希冀有丰裕的收成,扁豆就这样徘徊在非正式菜蔬的边缘,而这一点,也让它保持了恰到好处的野性,偶尔尝尝,才叫人欲罢不能,念念难忘啊。
对了,据我所知,扁豆还有一个名字是我们无论如何想破脑袋都想不到的,在通城文友卢老师的笔下,它被唤作羊阿结,这哪里是乡言俚语,简直是打英文翻译过来的嘛,羊阿结,羊阿结,一个同样充满了野性光彩的名字,叫人匪夷所思,又叫人浮想联翩,扁豆的这一生啊,还真是不容小觑!(图片源于网络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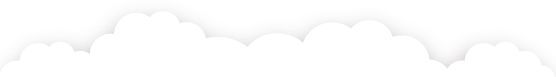
主 编:阮冰
编 辑:葛素文
编 审:阮翀
监 制:方雷
总监制:阮班新
出品人:阮胜利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