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过年在老家拎来一袋红薯,可惜时节不等人,惊蛰过后,种子们都苏醒了,没来得及吃完的红薯,长上了细细的小芽。
以往,从菜市场买回的土豆要是发芽了,随手就扔了。可是,红薯不一样。它是老家来的,周身还粘着老家的土粒,对于我这难得回家一次的游子来说,见了它就有一种温馨亲切的感情,怎么说也是扔不下手的。要是在田肥地沃的老家,插进土里就能长出一株茂盛的薯藤来,只是如今繁华忙碌的生活里,却委屈了这颗随我而来的小红薯,委屈了这颗在春风中醒来却又无处安身的小种子,心头万分惭愧。


小时候,红薯是家中粮食的主力军。每年总要收上二三十担,好的大的选出来装满一整个薯洞,薯洞可大了,向阳的半山腰上挖的垂直四五米高,直径至少有一米长的洞,顶上盖着丝茅做的能躲雨透风的茅顶,红薯放在里面就能稳稳妥妥的直到春后,一直新鲜。想吃的时候,用麻绳系着箩筐放下去装,一担担挑回家里慢慢吃。每年秋后,家里总要腾出半间房来装那些挖破的、个头小的薯脚,每天焖一大锅,倒进猪食槽,大猪小猪吃得可欢了。
春头上,口渴的时候,家人也会削上几个薯心,煮一碗薯汤,沁甜沁甜的,清新爽口。
可惜,这只是一段离我越来越远的记忆。


小时候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,每天羡慕的都是山外的世界。大人也总在想方设法,通过各种诱惑激发我们的斗志,焕醒我的梦想,将来必须要走出大山,做个有出息的人。对于我们来说,能够改变命运的唯一稻草就是读书,所以,兄弟姐妹们都卯足劲拼命读书。一个个,终于,沿着这细窄的田堘小道,穿过一丘丘稻田、一片片薯地,在父母欣慰的目光中,在我无比羡慕的眼神里,搭上通往城里的班车……


我是小的,所以总在见证着哥哥姐姐离开的样子。他们刚教会我玩过家家、捏泥巴,就搭着班车去城里了。每一次班车在小站停下的时候,都恨不得跟他们一起跳进去,可一次次的都在哥哥姐姐的抚慰中软下来,看着班车启动,离开,在卷起的一大团灰尘中消失,直到灰尘落地,小山里恢复宁静,我才带着说不出的伤感再沿着田堘小道走回家。即便脚上穿着母亲刚做好的新式样的泡沫底花布鞋,喜悦感还是超越不了失落感。
长长的日子,我都是孤独地在家里玩泥巴,过家家。晚上,趴在桌台上看煤油灯的火焰一点一点吸收灯管里的油,照得整个房间亮堂堂的,墙壁上那泥巴砖一块一块垒成的鲜明痕迹,像父亲胸膛强壮的腹肌;地面虽然是凹凸不平的,可曾经也用木巴掌锤得十分光滑,就像母亲细腻的脸。满满的一灯管的煤油,被小火苗一口一口舔走了;又或者,走出院子,望望头顶的星星。


后来,我也如愿走出来了,刚离开小村的时候,特别兴奋,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。
终于,不用一整个夏天都吃辣椒炒茄子、炒豆角、炒苦瓜;也不用一整个冬天都是小土钵里炖得滚咆咆的辣椒皮、干豆角、干咸菜;不用整天只听鸟儿嘈杂的叫唤,偶尔夹杂一两声狗吠、一两声鸡啼;城里的白天黑夜永远不知疲惫,宽阔的马路上永远都有悠扬悦耳的鸣笛声,多热闹啊!多鲜活啊!城里人多幸福啊!就连炒菜的声音都那么好听,锅勺轻轻相碰,发出清脆的叮当响,不像老家嵌在灶堂里的锅,永远都是一副沉闷的调调。就像那些闷不吭声的老伯,只知埋头耕作,双脚踩在大山的脊背上,步调沉闷闷的,没有一点儿声响。


我着实被城里的生活迷住了,就这样,与老家越来越远。
毕竟,是老家的水土滋养我长大,这种情感是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。在城里吃过各种名贵的菜后,最怀念的,还是家中锅灶炒的那些青椒豆角、茄子、苦瓜,是土钵中炖得香喷喷的干咸菜、干豆角,还有炭火偎熟的红薯。
纵使我经过千般努力过上了新生活,面对一颗发芽的红薯,却无力安置。对家乡的愧疚,油然而生。
周末,在花草市场淘来养花的土和盆,满怀歉意地把芽薯埋入。只是不知道这薯能否安心,在这灯光摇曳的城区,是否也会如我,长出一缕零乱孤寂的乡愁,长出一腔对家乡故土的愧疚?
在乍暖还寒的雨夜,在民工歌手“旭日阳刚”的《春天里》,在略显寂寥的阳台,我这一只老家走出来的红薯,一只怀念老家乡音的薯,长芽的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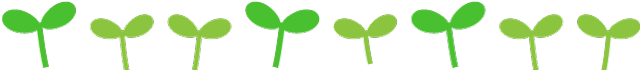
编后语:地球是一个村,对通山,对亲人,对故乡的挂念,来自北京上海,深圳沿海,纽约巴黎,武汉咸宁,大畈黄沙,都没有两样,上屋到下屋就是客,从年龄上无须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从“颜值”上不必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这就是我把袁丽明的“长芽的红薯”放到《乡音》来的理由。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,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,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上,而是,用自己冷漠心去对爱你的,掘了一条无法逾越的沟渠”。唐代贾岛的《题诗后》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。多年前,我有过知识性笑话,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库区的散文,对照相器材知识欠缺,把柯达胶卷理解为相机品牌。对于谦虚的新秀作者,我除了认真拜读佳作外,尽我所能作些“画蛇添足”式润色,包括知识性的东西,如她把薯洞直径写成两米,“人”字型跨脚下去装薯,怕是要掉进薯洞了,在前几日朱必毅《走出大山》的新书座谈会上,我就和她笑谈这个秘密,穷人后代的我,几岁时跟在老父背后,常常到薯窖起过薯。不比土豆,长芽的大蒜只要没有变色发霉腐烂也是吃以吃的,如此等等。凤头、猪肚、豹尾,这是新闻写作的手法,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,好多小小说的包袱就是这样情理之中抖开的。
通山广播电视台APP云上通山文学作品投稿邮箱:365278228@qq.com,附与文字有关的图片6张,个人简介及个人图片,让更多人见证你“搬砖历程”。(方雷)



作者简介:袁丽明,女,现供职于通山县文化馆,用心读书,感恩生活。将真情流淌于笔尖,用文字净化心灵。在读与写的世界里,遇到更好的自己。

编 辑:徐 微
编 审:乐有钦 唐尚伟
监 制:方 雷
总监制:阮胜利





